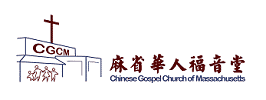【我的信主经历】- 徐志雄
从小的梦想是当个科学家,在众人面前宣告我的科研成果,造福人类。多年之后,我却站在了教会的讲台上,在众人面前传讲上帝的话语,希望把神的恩典告诉每个人。神好像给我开了个大玩笑,但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,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
最早接触神,是在大学的时候,也许是89那阵子收听“敌台”,却意外地听到了香港的福音电台,里面讲,“宇宙这么大,你怎么能说没有神?”,我一听,心想这叫什么逻辑,宇宙这么大,你倒找个神给我看看?于是非常淡定地将电台转到了“造谣之音”。
6.4之后,心里的失望可想而知,毕业时正好有公派日本的机会,就去了东京,在街头偶遇小学同学,一见如故。他问,“想不想发笔小财?”我说,“怎么讲?”他说,“请跟我来。”
跟着他来到日本人最喜欢玩的Pachinko(打弹子机赌场)。第一次去,里面的场面还是蛮震撼的,皇宫似的富丽堂皇,一行行的机器,一排排的客人,时不时听见中奖后弹子哗啦啦倒出来的声音,非常地诱人。
他带我到一台比较僻静的机器旁坐下,交给我1万日元,说,“你试试手气,输了算我的,赢了我们对分。”我将信将疑,居然有这种好事,那就试试吧。
半个小时之后,我们拿着赢来的10万日元走出Pachinko。
到了外面,我急忙问他:“怎么回事?”
他诡秘地眨眨眼睛,“你运气不错。”
“少来这套,这里肯定有猫腻,你怎么知道会赢?”
他哈哈一笑,“好吧,实话跟你说,你玩的那台机器我们做过手脚。这里的服务员是我们自己人,晚上没人的时候,他将一个电子开关放进那台弹子机里,你打的时候,我只要按一下口袋里的遥控器,机器就开奖了。”
我半信半疑,“有这样的好事,那你自己发财就是了,拉上我干嘛?”
“同一个人天天在那台机器上赢钱,目标太大,换个人比较隐蔽一点。不过,这也不是长久之计,过两天就不能再用那台机器了,不然迟早会出事的。”
“那你让内应把电子开关换到另一台机器上不就完了?”
他叹一口气,“你知道什么呀,pachinko老板已经有点怀疑了,我们的内应这个星期做完就要走人了。好了,不说这些了,我们去撮一顿,庆祝一下。”
于是我们找了家饭店,两个人坐下边吃边聊,他问,“你大学是什么专业?”
我说,“电子工程。”
“奥,太好了,吃完饭,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我问,“是谁?”
“一个朋友,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出了饭店,跟他来到他的住处,一间小小的房间,阴阴暗暗的,里面出来一个瘦高个,人称”长脚”。彼此介绍一番,寒暄过后,谈话进入正题。长脚说,“我们想做更大的买卖,需要你这样的电子专家。”说着,从房间的角落里搬出来一台机器。我问,“这是什么?”他说,”这是pachinko里面数弹子的机器,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的原理,直接在这上面做手脚,那风险要小得多,怎么样,看你的啦。”
我心中一动,学了四年的专业,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。现在回头想想,实在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,感情我十多年用功读书,最终是为黑社会服务来着。我看了看机器,心里有了6,7分把握,说道,“这个我不敢打包票,尽力而为吧,不过我要找个帮手。”他俩异口同声,“没问题。”
从同学这儿出来,回到家,我找来了和我一同赴日的小Q,他是我认识的电器高手,动手能力极强,当年电子线路课做实验搭电路板(俗称面包板),大多数人若能把结果做出来就欣喜若狂了,而小Q搭的面包板,不但功能强大,而且做的象艺术品一样,连老师都赞不绝口。若是有他相助,我大概至少有九成的把握。和他一谈,我们一拍即合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我们居然学有所用,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了,只是那个社会颜色有点深。


一个星期之后,我们的“技术攻关”有了突破。数弹子机的原理其实不复杂,机器主体由三部分组成,上面一层是紫外线发射器,中间一层是弹子通道,下面一层是紫外线接受器。当没有弹子通过的时候,上层发射的紫外线被下面的接受器接受,大家相安无事;当有弹子通过的瞬间,弹子正好把紫外线挡住,接受器就接受不到信号,这就相当于在电路系统上就产生了一个脉冲,计数器就加一。把原理搞明白了,下面就好办了,如果我们有一个电子脉冲发生器,对着接受器发射,效果应该是一样的。
我和小Q兴奋莫名,连夜杀奔秋叶原--东京著名的电子元件市场,两个小时之后,我们回到住处,迫不及待地要验证我们的想法。在昏暗的灯光底下,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了数弹子机的显示屏,我接通了脉冲发生器,对准数弹子机的接收层,将发射频率逐渐加大,1,2,3,4,5,6 ……. 计数器飞速地跳动起来,越跳越快,我们成功了!
“长脚”一拍大腿,“好,太好了。我去找老大来,我们开个庆功宴。”
老大是个壮实的中年人,臂上挽着个台湾美女,两眼炯炯有神。他举起酒杯, “好,大家这几天辛苦了,有了这个高科技的东西,我们这回一定发大了。等这笔买卖干完,我去弄几只冲锋枪来,这块地盘就是我们兄弟的了。”
听了这话,我心里一沉,成功的喜悦被冲走了一大半,心里想:莫不是还真的沾上黑社会了。
庆功宴之后,老大和长脚从此杳无音讯。一天一天地就这样过着,我心里的那一丝担忧也渐渐地淡漠了,反倒有了越来越多的期盼和喜悦,因为我要结婚了。
未婚妻是我大学同班同学,毕业时我们却阴差阳错,一个到了日本,一个去了美国。当时我一心想的是去美国和她团聚,于是便想和公司商量,辞了工作,办因私护照去美国,领导明察秋毫,“你想辞职去美国是不可能的。你的档案在我们手里,我们是不会放人的。公司既然要了你,就不要多想别的了,专心学日语去日本吧。”
没办法,只好曲线救国,先结了婚,再申请去陪读总可以了吧。可是要结婚就得先开未婚证明,领导当然不是吃素的,一眼就看穿了我的“阳谋”,“我们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,因为你在日本是不能结婚的。”
我急了,“能不能在日本结婚,我自己会想办法,可是你得先给我开未婚证明,我是适婚青年,你没有理由不给我开呀。”就这样软磨硬泡了好几天,终于领导松口了,“这事我作不了主,你得找总经理。”
总经理是日本人,没办法,只好壮起胆子,直接和总经理谈。结结巴巴和他讲了半天,他终于明白了我想要结婚,于是问我,“你要结婚,找我干什么?” Good question!我也不想找你,可是没办法,这是中国特色。于是又费了半天的劲儿,解释没有他同意,我就没法拿未婚证明,没有未婚证明,就结婚的没有。老总终于明白了,呵呵一笑,“No problem,结婚去吧。”
就这样,过五关斩六将,去拿各种各样的证明。最有意思的去开无艾滋病证明,日本医生一脸严肃,“Jo San,你为什么觉得你会得艾滋病?”嘿嘿,不为什么,被逼无奈而已。
终于手续都搞齐了,开始忙着操办起了婚事。就在这节骨眼上,又在路上碰到了我的同学。
我心里还惦记着我们的“高科技产品”,也不知道“老大”买了冲锋枪没有,于是问他,“那事到底最后怎么样了?”
他一脸苦笑,“黄了,真倒霉, Pachinko 更新换代,把数弹子机都换成新的型号了,我们的发射器一次也没用上。”
听了这话,我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不管他讲的是真是假,反正我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。他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的意思,话锋一转,问道,“最近在忙些什么?”
“啊,忙着准备结婚呐。” 我答道。
“行头置办得怎么样了?西装领带皮鞋,都有了?”
“都是原来从国内带来的,日本的衣服太贵了。”
他眼睛一亮,“结婚是人生大事,不能太随便了。这事你别管了, 包在我身上。”然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,“我们俩身材差不多,你跟我来。”
跟着他来到东京最繁华的银座,到了一家服装店门口,他把手中的塑料袋往我这儿一塞,说,“你在门口等我一下,我去去就来。”说完,整了整衣服,挺起胸,气宇轩昂地走了进去。我心里隐约猜到又有事要发生了。
果然,二十分钟之后,他腋下夹着个公文包,鼻子上多了一副眼镜,西装革履,一身名牌地走了出来。他不紧不慢地来到我跟前,说,“别发呆了,走吧。”
我站在那儿,目瞪口呆。
晚上,我迫不及待地给未婚妻打电话,“Honey,我结婚的行头置办齐了,都是日本的名牌。”她嗔怪道,“花那么多钱干什么?我们在上海的婚礼还要一大笔钱呢。”我喜滋滋地说,“别担心,猜猜我是从哪里搞来的。”“猜不出。”“实话告诉你吧,这是我同学从银座的名牌店里偷出来的。”“What?”这回轮到她目瞪口呆了。电话那头沉默良久。“怎么啦?”我问。她迟疑了一下,终于开口了,“你以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放下电话,我陷入了沉思,我这是怎么了?几年前我还自认是个有志青年,为了国家和民族,一腔热血,上街游行,要清除腐败,要打倒官倒,梦想建立一个民主公正富强的社会;几年过后,我竟然沦落到了黑社会的边缘 …… 我的心里一片迷茫,只有一个念头,“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,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”这好像是我唯一可以抓住的那一根稻草。
现在回头看,在日本的这段经历,对我后来愿意接受基督教有着很大的影响。许多中国人接触基督教,常常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,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是罪人,人里面有罪性。这和儒家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是不同的。而对我来讲,这一点却完全不成为拦阻,因为我知道,我之所以从小到大还算个好孩子,就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环境,有好的父母,好的老师,好的同学,要想变坏也难。可是换了一个环境,稍稍多一点诱惑,我里面的罪性就如此地滋生壮大,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可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自我反省,让我在那一位公义的神面前不由自主地谦卑下来,不再那么理直气壮。就像美国人常常讲的,“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,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.”
当然,前提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存在,要让一个从小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,满脑子逻辑,证据,进化论的我去相信的确有神,绝非易事。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,晴空万里,一架波音737客机缓缓降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Albuquerque机场。我和妻子终于在美国团聚了。
一个月之前,我第三次踏进了日本的美国领事馆,递上我被拒签了两次的护照。 给我签证的女签证官翻了翻我的签证纪录,缓缓地对我说,“对不起,我不能给你签证。”我心里一沉,她接着说,“因为我上次对你拒签了,为了公正起见,这一次,我请我的同事来审阅你的材料。”吓死我了,不带这么大喘气的。
转到另一个窗口,是一个高高瘦瘦的金发俊男,他看了看材料问,“你去美国干什么?”我答,“我妻子在美国念书,我想拿F2签证去陪读。”“按照规定,我不能给你F2签证,因为你有移民倾向。”他顿了顿,向我眨了眨眼睛,“不过,你在日本的工作很好,公司背景也强,你可以申请旅游签证去美国,你愿不愿意?”我几乎要感激涕零了,因为他的一念之慈,我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了!
临走前一晚,我们一同赴日的几个好朋友相聚在上野的一家中国餐馆,为小z举行告别晚宴,因为第二天一早,他就要离日赴美了。我当时挣扎了许久,要不要向一班好友透露,我也要走了,我的航班和小z只相差2、3个小时。但是我还是忍住了,我不想在最后一刻,节外生枝。
我的谨慎其实并非多余,后来才知道,我和小z的同时离去在当时震动极大,公司当局一直追查我们的下落,直到最后动用了关系,查明小z飞赴纽约,我在休士顿入境美国,才算罢休。随后,公司又企图收缴所有公派同学的护照,引起大规模的抵制,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现在想来,真是强扭的瓜不甜,若中方领导当年不强行送我去日本,也就不会有两年后这场“逃出日本”的闹剧了。其实公司待我们还算不错的,真的把我们当成人才来用,给他们带去那么多的麻烦,实在是有点对不住他们。
离开日本,我的感觉就好像鸟儿飞出了笼子一般,在Houston过关的时候,海关的官员问我来美国干什么,我说,“我妻子在美国念书,我来看她。”他说,“你的签证搞错了,B2签证只能在美国待一个月,我无法给你更多了,你赶紧找律师换成F2签证吧。”刚刚踏上美国国土,我就深深地被普通美国人的善良仁厚,通情达理感动了。
在Albuquerque最先认识的美国人是道生教授和他的妻子琳达。道生是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,也是新墨西哥大学的客座教授,矮矮的个头,两道浓眉,脸上永远带着和蔼可亲的微笑。他是我太太的老师,拿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般,也就是他们两口子把我们带进了教会。
说实在,我走进教会的动机实在是非常功利的,一方面是感激道生夫妇对太太的照顾,盛情难却,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教会里多和美国人打打交道,练练口语。所以牧师讲的我基本上是一个耳朵进,另一个耳朵出,什么都没记住。而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道生教授这个人。
原来以为信教的人,都是些没有文化的老太太,要不就是失恋的,失意的,失望的加上失败的。从来没有想过象道生这样的杰出科学家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,后来慢慢地才知道结婚之前道生是不信神的,而琳达却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,结婚之后,为着信仰的不同,两人屡屡发生冲突。从小循规蹈矩的琳达哪里是能言善辩的道生的对手,常常被道生呛得哑口无言,最后有一天,琳达对道生讲,“好了,我们不要再吵了,你是一个作研究的人,最讲究用证据说话,你去找证据来证明我信错了,我就听你的。”
于是道生就真的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,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道生最后决定信主了。因为他看到的证据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信仰归宿。
虽然道生提到的那些证据对我来讲,实在是听得个一知半解,稀里糊涂,但是他的学识和为人却让我从此对基督徒刮目相看。
在Albuquerque的那几个月,快乐而又忙碌。买旧车,学驾驶,考执照,找工作,申请学校。生活充满了等待和期盼,终于在夏天开始的时候,一家远在麻州的保险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,聊了几句之后,发现我在日本做的软件开发和他们这里的完全一样,于是连面试都省了,直接就决定录用我。而且他们愿意替我办绿卡,这样身份问题也解决了。那几天就好像在做梦一般,我和太太都无法相信我们会如此地幸运,因为那时其实internet还没有起步,美国经济也不景气,许多留学生毕了业,却因为身份的关系找不到工作,只好继续读博士或者做博士后。91年底爱荷华大学的卢刚事件,起因就是卢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,结果迁怒于他的教授和同学,枪杀6人之后,饮弹自尽,这是题外话了。
我找到了工作,太太也硕士毕了业,我们就要告别朋友和导师,离开永远阳光明媚的Albuquerque了。得知我们要走了,道生夫妇依依不舍,拉住我太太的手,问她愿不愿意在走之前受洗,成为基督徒。她不假思索地回答,“我愿意。”我倒是吃了一惊,这种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。
回到家,我问她,“你真的要受洗啊?”
她说,“是啊,他们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,要是有天堂,我是要去的。”
“那我怎么办,你就这样扔下我,一个人去天堂?”我半开玩笑地问。
“你要想去,你也可以受洗呀?”
我哑口无言。对一个根本不相信上帝,不相信天堂地狱的人,受洗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,但妻子愿意,我也无所谓,只要她高兴就好。让我吃惊的倒是教会里的人欢天喜地的样子,好像过节一般,妻子受完洗,大家纷纷送上礼物,兴高采烈。当然最高兴的是道生夫妇,送来了一大簇的鲜花,拉着我太太的手,说着祝福的话,脸上流露出发自心底的喜悦,浑身散发着爱的光辉,那一刻,让不信神的我也被他们的真挚所感染,被爱的感觉真好。
要离开了,心里依依不舍,但又充满期待,因为我们的美国梦即将要开始了。此外,心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没有了道生夫妇,我就再也不必为去不去教堂纠结了,再说太太也受洗了,她天堂的门票也拿到手了,我的教堂生涯也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吧。
94年夏天,把一家一当--四只大旅行箱塞进那辆白色的Hatchback,我们就上路了。一个星期的时间,我们走走停停,横穿半个美国,来到了东岸。感受最深的就是放眼望去,到处是郁郁苍苍的树木,满目葱茏,和新墨西哥一望无际的灰黄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这里有山有水,有花有草,在往后的二十年里,美丽的新英格兰成为了我们的第二故乡。
拿到了第一个月的薪水,忽然发觉我们好有钱,于是两个人决定吃遍Boston的中餐馆,一个星期一家,好不自在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快乐地过着,我们早已把教会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,直到有一天,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:“请问,这是不是徐先生,徐太太的家。”
“是,请问您是哪一位?”
“啊,我是这里华人福音堂的章开第传道,你们的朋友道生夫妇委托我向你们问好。也欢迎你们到我们这里的华人教会来看看。”
道生夫妇还真有心,千里之遥居然还辗转找到这里的华人教会,委托他们来照顾我们。在章传道的力邀之下,我们再一次踏进了教会。
毕竟中文是母语,到了华人教会就好像有回到了家的感觉。第一次正好是教会的徐长老在讲解创世纪伊甸园的故事,我从来是把亚当夏娃的故事当作神话来看待的,可是这位长老居然能把这一段讲得头头是道,像是真的一样,这对我来讲可谓是一次启蒙,原来基督徒是这么解读圣经的,他们是把圣经的记载都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,而且他们宣称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,所以“圣经无误”。这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和好胜心,我心想,我就不信这里面会没有丝毫的纰漏,我的读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

秋天的时候,太太在耶鲁附近找到了工作,和我的公司相距150英里,思来想去,最后决定替她在耶鲁附近找处小公寓,这样至少我们周末可以在一起。这事让教会里的一位在康州工作的弟兄知道了,就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去那边找房子。
那年代没有互联网,你要找房子必须到那个地方,找到当地报纸的星期日广告版,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问,要是当地没有熟人的话,是非常不方便的。
我们找了一个周六,搭这位弟兄的车来到了康州他的一位姓孙的朋友家中,当晚就在孙弟兄的家中住下了。孙弟兄两口子是从台湾来的基督徒,儿子刚上大学,我们就睡在他们儿子的房间里,孙太太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,热情好客,给我们看她儿子的各种照片和奖杯,和我们聊家常,待我们仿佛是远道来的亲戚一般;孙弟兄黝黑的皮肤,瘦瘦高高的一个人,要讲的话一大半都被太太抢去了,于是只好看着我们笑,非常可爱的一家人。虽然我们相差了十多岁,又是海峡两岸不同的背景,可是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们,这是真诚和善,让你可以信任的一家人。
第二天一早我们醒来,孙太太已经做好了早点,久违的豆浆和包子,在饭桌上冒着热气,旁边放着当天的报纸,厚厚的一叠广告,正是我们需要的。
我心里暖暖的,在日本也好,在国内也好,经历各种的尔虞我诈,勾心斗角,奉行的是见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,总是提防着不要被人骗了,或是被人占了便宜。而在这里,我看见却是教会里的人,对你完全地接纳,不问你的身份地位,只要你有需要,他们就愿意尽他们的力来帮你一把。我相信这正是基督教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在孙弟兄夫妇的帮助下,我们很快在New Haven附近找到了房子。一间小小的公寓,一张饭桌一张床,再加上两把椅子,就是全部的家具了,虽是简陋,但却是一个温馨的家。每个星期五下了班之后,我就从麻州开两个半小时,回到New Haven的家,然后星期一的早晨,起个大早,再往回赶。虽然辛苦,但因为年轻,所以也不觉得什么。只是遇上风雪天就比较麻烦,有一次遇上暴雨,把雨刷开到最大档,还是看不清前面的路,只能依稀跟着前车的尾灯往前蹭,最后索性把车停在了高速公路边,看着车窗外的狂风暴雨,一筹莫展。
更讨厌的是大雪天。那次是星期一大清早,我心急慌忙往公司赶,结果车子打滑,擦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。天还是乌黑乌黑的,路上一辆车也没有,借着昏暗的路灯,我查看了一下受损情况,我的车倒还好,只是车前方右侧的挡板有些擦痕,而对方的车就惨了,左前门被撞变了形。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几秒钟,一个声音在说,“要不要留下电话地址,告诉人家是你撞的?”另一个声音却道,“本来就是辆旧车,留下电话,会不会被人家狮子大开口讹诈?反正没人看见,快溜吧。”终于良知的声音被压下去了,我钻进车子,仓皇逃离了现场。
到了公司,同事看见了我的车受损,关心地问我,“出车祸了?”,我只好支支吾吾地说,“嗯,不小心自己撞到了墙。” 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遮盖。
这之后,每当我看见圣经上讲,“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”,讲到魔鬼“本来是说谎的,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”我就心里一颤,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,无声地见证着我的亏欠。
多年之后,上帝给了我第二次的机会。太太倒车撞到了停在路边的车,这一次,我老老实实地敲开了人家的房门,“对不起,我们不小心撞到你的车了。”没想到车主人查看了一下伤痕,竟然大度地对我们说,“没关系,一点点擦伤,我自己处理就是了,要是花费太大,我再找你们,好不好?”
除了谢谢,我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。对我来讲,这不堪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,上帝让我看到,即便是做老实人,也不一定就会吃亏。
在纽黑文的那段日子里,生活简单,但不枯燥。周五的晚上就去孙弟兄的家,有聚餐,有查经。孙弟兄话不很多,人却极其真诚,慢慢知道了他原来是修行很深的佛教徒,花了很多的时间钻研佛经,最后却变成了基督徒。于是就很有兴趣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改变信仰的。
他说,“信佛让我向善,可是我却发现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;基督教不仅让我向善,而且给了我行善的能力。”
他讲的前半句我大至可以了解,这让我想起当年白居易和鸟窠禅师的一段对话:
白居易请教大师佛学的精义,鸟窠禅师给了他八个字: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。” 白居易听后哈哈大笑,“这个道理,三岁小儿都知道。”大师回答:“三岁小儿虽道得,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
讲的也许就是这种无力行善的困境吧。可是孙弟兄的后半句话,我完全无法了解。于是他就给我解释,这是一种从神而来的能力,做人所不能的事情。
他讲有一次他去探望一位台湾老将军,两个人聊到基督信仰,孙弟兄就讲人都是罪人,这下把将军惹毛了。他挺直着腰板,大声说,“我二十岁投笔从戎,为国为民,舍身忘死,上对得起天,下对得起地,我不是罪人!”孙弟兄当场就楞在那里,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然而心底里却不知为什么涌起一种悲悯的情绪,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,他本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,可是那一次不知怎么了,对自己拼命说不要哭,可眼泪就是停不下来,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,结果老将军长叹一声,说,“你是对的,我是一个罪人。” 原来将军年轻时曾辜负过一位女子,这事一直在他心底存着,从来没有向人提过,而那一天,将军向孙弟兄和盘托出,最后竟然在孙弟兄带领下信主了。事后,他夸孙弟兄,“你真会讲话,竟然把我说动了。”
孙弟兄笑着对我说,“其实那一天我基本就没讲什么话,只是神的灵在那里做工,感动我,也感动老将军,让他信了主,这就是我讲的从神那里来的能力。”
孙弟兄的故事,对我是一个冲击,难道真的是有超自然的能力,真的有神?
我是学理工科的,多年的训练让我对任何事都不会轻易相信。对任何的宣称,我们不但要看证据,更要看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。
举一个例子,我在教会认识的一位朋友,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看见她,最近在一次烧烤的聚会上碰到了,彼此问候之后,我就问她,“怎么好久都没看见你,还好吗?”
她说,“现在还好,前两年生了一场大病。”
我问,“怎么了?”
“脑子里生了个瘤,美国医生都没什么办法,后来是朋友介绍,练了**功,瘤子就没有了。所以我现在信**功了,也替他们做一些义工,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
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,其实我很理解她的选择,这种神迹般的医治,对人的世界观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。可是,站在朋友的立场,我不得不告诉她,她的选择可能会有问题。因为她认定是跟着师傅练功,才医治了她的疾病,这里的因果关系其实并不那么确定。我有一些朋友是从事癌症药物开发的,从他们专业的角度来讲,判定一个药物是否有效,看一个个案是完全没有意义的,人体有许多的机能我们还不明白,有些人会对不含任何有效成分的安慰剂有反应,也许是某种心里的作用,有时也能得医治。所以判定一个药物是否有效,最好是用双盲试验,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用的是安慰剂还是真的药物,这样出来的结果才会有意义,才能判断这个药物是否真的有效。
当然对我这位朋友来讲,她不见得关心练功的医疗效果,即便在其他人身上没有任何效果,可是对她来讲,她得了医治就够了,用她的话来讲,也许就是因为她是有缘之人。
这就牵涉到许多人都有的第二个误区,就是认为灵验的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,从她的观点来看,因为练了大法,病得医治,所以*大师讲的就一定是对的,是宇宙的真理,真神的化身。其实,各大宗教都有神迹奇事,佛教,基督教,伊斯兰教,甚至连一些明显的邪教都有神迹发生。站在基督教的立场,这不足为奇,基督教认为神迹,或者超自然的事会发生,除去骗人的把戏和人为的巧合,无非有两种可能:一种是从神那里来的,一种是从魔鬼那里来的。这两种灵界的力量都能做人所不能的事情,只是人常常轻信,以为神迹就一定是从神而来,其实不见得。圣经讲的好:“一切的灵,你们不可都信,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於神的不是。”
回到孙弟兄讲的故事,虽然让我感动,但是让我象老将军那样就这样信主,我觉得还有不够的地方,我需要实在的证据。如果说道生夫妇,让我对基督徒心生好感的话,那孙弟兄就是我信仰的引路人,因为从他的书架上,神让我找到了我要看的证据--麦道卫(Josh McDowell)写的《铁证待判》。

《铁证待判》的作者是学法律的,他好像道生教授那样,接受人家对他的挑战,去考察耶稣说自己是上帝儿子的宣称,结果他找到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证据,写成此书。他从法律审判的角度来检视这些人证物证,从而得出结论,你无法只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教师或圣人来看待,因为他的宣称太过惊世骇俗,耶稣若不是疯子,骗子,那你就不得不相信他的宣称,他是神的儿子。
看完此书,让我对基督教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,那不是一个只诉求于你的主观经历的信仰,不是讲缘分,也不是讲慧根,它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摆在那里,任何人只要你愿意,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神,就好像耶稣讲的,“你们祈求,就给你们;寻找,就寻见;叩门,就给你们开门。”
在孙弟兄的帮助下,我对基督教的认识逐渐加深。而另一方面,一个冬天的奔波,让我们决定还是搬家住在两人公司的中间地带,这样虽然辛苦一点,但至少可以每天在一起。开春的时候,我们离开纽黑文,搬到了康州的首府Hartford。我每天单程开车90英里(145公里),太太单程60英里(97公里),仗着年轻力壮,就这样开始了我们“疯狂的旅程”。
那时在孙弟兄的介绍下,我们找到了Hartford的一家华人教会,从那里借了许多布道会的磁带在开车的时候听。在我每天单调的旅程中,这些磁带带给了我许多的欢笑,鼓舞和思考,每天晚上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和太太分享白天听到的信息,互相探讨切磋。到了星期五的晚上,我们拖着劳累了一周的身体来到那间华人教会,听带查经的弟兄讲解圣经,和大家辩论,等到结束,走出教会的时候,身心的疲乏竟然完全被洗去,人好像重新充了电一般,就这样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成了我每周的期盼。现在回头想来,神实在是恩待我,让我有渴慕的心去寻求他,也借着各种各样的人来回答我心里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而其中一直困扰着我的,就是关于灵界的问题。
小时候最害怕又最爱听的,莫过于奇奇怪怪的鬼故事了。夏天的晚上,吃过晚饭,搬只小凳子,坐在弄堂深处,听隔壁邻居家的大孩子,讲《一只绣花鞋》,《绿色的尸体》之类的吓人故事,在那闷热的夜晚,给人后背带来一丝丝的凉意。
在中国的民间传统里,认为人死后就变成鬼。好人变好鬼,如果受大家爱戴的,可能还会升格成神仙,象关羽,包拯一样;而坏人死后变成恶鬼,有时还会为害人间,需要有道士和尚来制服他们,所谓“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到了天朝初期,破除一切封建迷信,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深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,对一切鬼神之谈往往嗤之以鼻 。所以许多人看到圣经中描述耶稣赶鬼的故事,就象看聊斋志异一般,只是把它当成民间传说故事来看待。
我当然也不例外,在查经班屡屡挑战老师的底线,成为教会有名的问题儿童。直到有一次,我们在热烈讨论灵界的真实性的时候,往常和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慕道友小C,突然反戈一击,说道,“我相信灵界的存在。” 于是小C就给我们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:
小C是练气功的,虽然来教会之后,有人提醒他练气功有一定的危险性,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有天晚上,他和往常一样打坐练功,渐入佳境之时,忽然看见一只右手从空中浮现,朝他的心口逼近,并且作势要掏他的心,这一下把小C吓得魂飞魄散,情急之下,他想起教会的人曾经对他讲过,在危难的时候,可以向耶稣祷告。于是他脱口而出,“耶稣救我!” 说时迟那时快,从天上仿佛降下一只巨手,一下子就把那只鬼手给提走了。
小C的故事,让我开始对灵界的真实有所了解。后来陆陆续续又听了梁燕城,张佳音等人的灵界经历,看了小光写的《冲破灵界的黑暗》,让我慢慢接受了圣经的观点。
圣经对灵界的事着墨不多,但看法和中国民间传统大不相同。基督教认为人死后是不会变成鬼的,而是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,直到神最后审判的那一天。在上帝所创造的所有活物中,最完美的是天使长,而这一位天使长却选择背叛,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反对神。这一位天使长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撒旦魔鬼,和它一起背叛的天使就是众邪灵。这些灵界的邪灵具有超自然的能力,他们有时祸害人,有时也选择“做好事”,但是目的都是一个,就是要让人远离上帝。它们最后的下场,是在审判之日被扔进火湖,面临永远的死亡。
写了这么多灵界的事情,希望不要给大家带去不安,请记得小C的故事,神比他所造的一切活物都大,在危难的时候,记得向耶稣祷告。
有些人会问,“你有没有经历过神迹?” 听过许多其他人的见证,可是发生在我身边的,我有十分把握的,也许只有一次。
那是我们刚信主不久,有一次太太要回国,结果在走的前一天感冒了,喉咙疼得火烧火燎,晚上她睡不着,于是就起来,跪在窗口向耶稣祷告,“主啊,我明天就要坐飞机回去,还想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朋友,可是现在这个样子,我真的担心连上飞机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主啊,求你医治我。”
基督徒也许都有过类似的祷告,我们也知道“这病不至于死”,迟早都会好的,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,只是想要一点从神那里来的平安,可以让我们好受一些。可是,那一个晚上,神迹发生了。
当她祷告完,人还跪在那里,没有完全站起来的时候,忽然好像有一个冰块从她的喉咙里通过,冰凉冰凉的,她人一下子站了起来,把我推醒,带着一种惊奇兴奋而又有些害怕地对我说,“神医治我了,神真的就在这里。”
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那一个晚上用神迹医治她,也许是因为我们刚信主不久,神要借着这来让我们知道他真实的存在?因为那时候,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,世上这么多的人祷告,神哪里管得过来?况且这个要出太阳,那个要下大雨,神听谁的好?一个老弟兄就对我讲,“神就是有这个能力,他听得到每个人的祷告。但是神不是我们得仆人,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行事。”
后来慢慢地我才明白祷告更多的是和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,就像谈恋爱似的,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,无话不谈,只要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和满足;如果只是需要帮忙了,才去找你的对象,那这两人的关系多半有问题。和神的关系也是如此,若只是有了需要才去求神,那你信的,其实是阿拉丁神灯的神,是你的仆人,不是你的主宰。
就这样,我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。有一天,太太问我,“你现在有几分相信?”
我说,“大概百分之八十吧。”
“那你要不要考虑受洗?”
我摇摇头,“你是知道我的,最烦教条的东西了。况且圣经上讲,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。我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了,不用走这个形式了吧。”
受洗的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。每天还是照常听着布道会的磁带去上班。这一天听的是徐华医生的讲道。在90年代的时候,徐华大概是在海外留学生中传福音最受欢迎的一位讲员,他本来是做麻醉科医生的,在事业顶峰的时候出来传道,带领无数的人信主,当年颇有今天唐崇荣牧师的影响力,而且两个人的风格也挺像的,幽默强势,咄咄逼人,和人们印象中牧师温文尔雅的形象大相径庭。可以看得出,他信主以前一定是个眼高于顶,非常骄傲的人。有一次讲道,他对着下面一班的留学生说,“不要以为你聪明,永远拿第一,那是因为你和我没有在一个班,有我在,你绝对别想拿第一……” 我们当年这批自视极高,气焰嚣张的留学生,也许正是被他的气势所压倒,又为他的口才和学识所折服,最终一个个在他的带领下信了主。
这一天,不知为什么,徐华忽然把炮火对准了那些自称信耶稣,却不肯受洗的人,“你算老几,竟敢说你不用受洗,连耶稣基督都受了洗,你自称为耶稣的信徒,倒不用受洗了?” 这话正中我的要害,对呀,既然我认为自己是信耶稣的,凭什么我就可以不听耶稣的吩咐,自说自话不用受洗了呢?那一天的感觉,就好像神借着徐华医生的口,把那一篇道讲给我一个人听。我无法再找借口了。
到了星期五,来到教会,我乖乖地找到了牧师,说:“我愿意接受洗礼。” 牧师反倒吓了一跳,没想到我这个不安定分子,居然自己提出要受洗了。可是下个主日就是浸礼,照理受洗的基督徒是要先上几个星期的受洗班的,总算牧师法外施恩,愿意破例为我补课。好在我大部分的问题都在这几个月的上班途中解决了,于是顺利过关。
1995年5月14日,母亲节。我和另外三位慕道友一同受洗,归入主名。从浸池里出来,天好像没有更加地蓝,草也没有格外地绿,我还是原来的我,但神的圣灵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到我里面,我生命的改变即将开始了。
洗礼完毕,牧师照例要祝福,轮到我时,他忽然打破常规,说起预言来,“弟兄,神让你这么辛苦,每天长途开车并不是偶然的,神要用这段时间,让你可以听他的话语,带领你归向他。如今你已经信主受洗,神的工作要告一段落了,我想你和你太太,过不了多久就不用这样长途跋涉了。”
一个月之后,太太工作换到了麻省,我们终于不用再长途跋涉了,牧师的“预言”应验了!
这是我们在十二个月里的第五次搬家了,从新墨西哥州开始,我们每搬一次家,就好像要离神远一点,可是他的慈绳爱索却紧紧地把我拉住,让我一步一步走进他的怀抱。回头去看,神好像是一个最有耐心的父亲,尽管我一次次地质疑,顶撞,甚至亵渎他,他却用他的爱吸引我,差遣他的仆人一个一个地为他作见证,道生夫妇,开第传道,讲解亚当夏娃的徐长老,开车送我们去康州的若珍弟兄,孙弟兄夫妇,梁燕城,张佳音,徐华医生。。。难怪圣经罗马书中这样描绘神的爱:
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,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,是少有的;为仁人死,或者有敢做的。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,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
而这才是个开头,在以后的十八年里,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,可谓数算不尽。超自然的神迹也许我们只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一件小事,可是若仔细去想,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改变,这本身岂不就是最大的神迹吗?俗话说得好,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易”,要能真正改变一个人,也许真的只有神的大能才可以做到。
我的性格是很急躁的,最明显的就是反映在开车上面。上了高速,我好像穿上了盔甲的骑士,风驰电掣,所向披靡。在信主的头几年里,我平均是一年两次车祸,一张罚单。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错,被我超过的车都开得太慢,根本就不应该在快车道上;把我超过的车都开得太快,统统应该被警察开罚单。神借着两件小事让我改变:
有一天,我在Masspike上飞车疾驰,到了收费站,一长串的队伍,我正心浮气躁,心里痛骂着州政府收刮民脂民膏,一个Big Dig挖了十五年,大大超出预算,只好用高速收费补亏空。这时一辆小车乘我一不留神,嗖地一下插到了我前面,我是气不打一处来,重重地按下了喇叭,嘟了他足足半分钟。可是插都插进来了,你有什么办法,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在我前面过了收费站,扬长而去。轮到我了,我把车开了上去,收费员向我挥了挥手,示意我走,我心里纳闷,州政府良心发现,不收费了?“Hi, what’s going on?”我问。“Oh, the guy in front of you has already paid the toll for you.” 原来前面那辆车可能有什么急事,插了我的队,感到不好意思,就替我把钱交了。我真是百感交集,忽然意识到我这个基督徒做得实在不怎么样,好像神在给我讲,“不要总是论断人家,要多一点谦让宽容的心。”
几天之后,我旧病复发,在高速上和一位老兄飙车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把坐在身边的太太差点气哭了,我也是一肚子气,每次我和人在路上有争抢,她总是站在我的反方,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。回到家,谁也不理谁,我进了书房,关上门,坐了一会儿,不知为什么,心里有一个冲动让我跪了下来,我刚一开口祷告,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,心里对自己的冲动鲁莽万分懊悔。要知道我已经是N年没有哭过了,上次去眼科医生那儿检查,医生说我泪腺有些堵塞,而这下应该是完全疏通了。正哭着,太太走了进来,手里拿着一个削好的水果,原来她在另一个房间祷告,神的灵也感动她,让她来和我道歉,不该总是给我火上浇油。这事之后,我在高速公路上的表现是可圈可点,连续多年无车祸无罚单,神就这样改变了我。
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,神对我的改变是全方位的,在夫妻关系,金钱奉献,教会事奉,各方各面,圣经好像是神写给人的一本使用手册,教导我们为人处事之道,让人一生行在神的光中。可以写的也许还有很多,只是到这里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。若是你要问,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好,神这么恩待我?我要告诉您,这个福分您也一样可以得到。圣经上说,
你们祈求,就给你们;寻找,就寻见;叩门,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,就得著;寻找的,就寻见;叩门的,就给他开门。
而且神所给的,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,因为“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,耳朵未曾听见,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”(哥林多前书2:9)
愿神祝福您!
cgcm_media July 17th, 2023
Posted In: DevotionTestimony, Testimon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