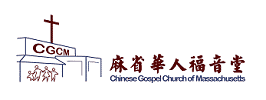【我的信主經歷】- 徐志雄
從小的夢想是當個科學家,在眾人面前宣告我的科研成果,造福人類。多年之後,我卻站在了教會的講台上,在眾人面前傳講上帝的話語,希望把神的恩典告訴每個人。神好像給我開了個大玩笑,但是他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,他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。
最早接觸神,是在大學的時候,也許是89那陣子收聽“敵台”,卻意外地聽到了香港的福音電台,裡面講,“宇宙這麼大,你怎麼能說沒有神?”,我一聽,心想這叫什麼邏輯,宇宙這麼大,你倒找個神給我看看?於是非常淡定地將電台轉到了“造謠之音”。
6.4之後,心裡的失望可想而知,畢業時正好有公派日本的機會,就去了東京,在街頭偶遇小學同學,一見如故。他問,“想不想發筆小財?”我說,“怎麼講?”他說,“請跟我來。”
跟着他來到日本人最喜歡玩的Pachinko(打彈子機賭場)。第一次去,裡面的場面還是蠻震撼的,皇宮似的富麗堂皇,一行行的機器,一排排的客人,時不時聽見中獎後彈子嘩啦啦倒出來的聲音,非常地誘人。
他帶我到一台比較僻靜的機器旁坐下,交給我1萬日元,說,“你試試手氣,輸了算我的,贏了我們對分。”我將信將疑,居然有這種好事,那就試試吧。
半個小時之後,我們拿着贏來的10萬日元走出Pachinko。
到了外面,我急忙問他:“怎麼回事?”
他詭秘地眨眨眼睛,“你運氣不錯。”
“少來這套,這裡肯定有貓膩,你怎麼知道會贏?”
他哈哈一笑,“好吧,實話跟你說,你玩的那台機器我們做過手腳。這裡的服務員是我們自己人,晚上沒人的時候,他將一個電子開關放進那台彈子機里,你打的時候,我只要按一下口袋裡的遙控器,機器就開獎了。”
我半信半疑,“有這樣的好事,那你自己發財就是了,拉上我幹嘛?”
“同一個人天天在那台機器上贏錢,目標太大,換個人比較隱蔽一點。不過,這也不是長久之計,過兩天就不能再用那台機器了,不然遲早會出事的。”
“那你讓內應把電子開關換到另一台機器上不就完了?”
他嘆一口氣,“你知道什麼呀,pachinko老闆已經有點懷疑了,我們的內應這個星期做完就要走人了。好了,不說這些了,我們去撮一頓,慶祝一下。”
於是我們找了家飯店,兩個人坐下邊吃邊聊,他問,“你大學是什麼專業?”
我說,“電子工程。”
“奧,太好了,吃完飯,我帶你去見一個人。”
我問,“是誰?”
“一個朋友,到時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出了飯店,跟他來到他的住處,一間小小的房間,陰陰暗暗的,裡面出來一個瘦高個,人稱”長腳”。彼此介紹一番,寒暄過後,談話進入正題。長腳說,“我們想做更大的買賣,需要你這樣的電子專家。”說著,從房間的角落裡搬出來一台機器。我問,“這是什麼?”他說,”這是pachinko裡面數彈子的機器,如果我們能夠找出它的原理,直接在這上面做手腳,那風險要小得多,怎麼樣,看你的啦。”
我心中一動,學了四年的專業,沒想到在這兒用上了。現在回頭想想,實在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,感情我十多年用功讀書,最終是為黑社會服務來着。我看了看機器,心裡有了6,7分把握,說道,“這個我不敢打包票,儘力而為吧,不過我要找個幫手。”他倆異口同聲,“沒問題。”
從同學這兒出來,回到家,我找來了和我一同赴日的小Q,他是我認識的電器高手,動手能力極強,當年電子線路課做實驗搭電路板(俗稱麵包板),大多數人若能把結果做出來就欣喜若狂了,而小Q搭的麵包板,不但功能強大,而且做的象藝術品一樣,連老師都讚不絕口。若是有他相助,我大概至少有九成的把握。和他一談,我們一拍即合,反正閑着也是閑着,我們居然學有所用,可以為社會做貢獻了,只是那個社會顏色有點深。


一個星期之後,我們的“技術攻關”有了突破。數彈子機的原理其實不複雜,機器主體由三部分組成,上面一層是紫外線發射器,中間一層是彈子通道,下面一層是紫外線接受器。當沒有彈子通過的時候,上層發射的紫外線被下面的接受器接受,大家相安無事;當有彈子通過的瞬間,彈子正好把紫外線擋住,接受器就接受不到信號,這就相當於在電路系統上就產生了一個脈衝,計數器就加一。把原理搞明白了,下面就好辦了,如果我們有一個電子脈衝發生器,對着接受器發射,效果應該是一樣的。
我和小Q興奮莫名,連夜殺奔秋葉原--東京著名的電子元件市場,兩個小時之後,我們回到住處,迫不及待地要驗證我們的想法。在昏暗的燈光底下,八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了數彈子機的顯示屏,我接通了脈衝發生器,對準數彈子機的接收層,將發射頻率逐漸加大,1,2,3,4,5,6 ……. 計數器飛速地跳動起來,越跳越快,我們成功了!
“長腳”一拍大腿,“好,太好了。我去找老大來,我們開個慶功宴。”
老大是個壯實的中年人,臂上挽着個台灣美女,兩眼炯炯有神。他舉起酒杯, “好,大家這幾天辛苦了,有了這個高科技的東西,我們這回一定發大了。等這筆買賣幹完,我去弄幾隻衝鋒槍來,這塊地盤就是我們兄弟的了。”
聽了這話,我心裡一沉,成功的喜悅被沖走了一大半,心裡想:莫不是還真的沾上黑社會了。
慶功宴之後,老大和長腳從此杳無音訊。一天一天地就這樣過着,我心裡的那一絲擔憂也漸漸地淡漠了,反倒有了越來越多的期盼和喜悅,因為我要結婚了。
未婚妻是我大學同班同學,畢業時我們卻陰差陽錯,一個到了日本,一個去了美國。當時我一心想的是去美國和她團聚,於是便想和公司商量,辭了工作,辦因私護照去美國,領導明察秋毫,“你想辭職去美國是不可能的。你的檔案在我們手裡,我們是不會放人的。公司既然要了你,就不要多想別的了,專心學日語去日本吧。”
沒辦法,只好曲線救國,先結了婚,再申請去陪讀總可以了吧。可是要結婚就得先開未婚證明,領導當然不是吃素的,一眼就看穿了我的“陽謀”,“我們不能給你開這個證明,因為你在日本是不能結婚的。”
我急了,“能不能在日本結婚,我自己會想辦法,可是你得先給我開未婚證明,我是適婚青年,你沒有理由不給我開呀。”就這樣軟磨硬泡了好幾天,終於領導鬆口了,“這事我作不了主,你得找總經理。”
總經理是日本人,沒辦法,只好壯起膽子,直接和總經理談。結結巴巴和他講了半天,他終於明白了我想要結婚,於是問我,“你要結婚,找我幹什麼?” Good question!我也不想找你,可是沒辦法,這是中國特色。於是又費了半天的勁兒,解釋沒有他同意,我就沒法拿未婚證明,沒有未婚證明,就結婚的沒有。老總終於明白了,呵呵一笑,“No problem,結婚去吧。”
就這樣,過五關斬六將,去拿各種各樣的證明。最有意思的去開無艾滋病證明,日本醫生一臉嚴肅,“Jo San,你為什麼覺得你會得艾滋病?”嘿嘿,不為什麼,被逼無奈而已。
終於手續都搞齊了,開始忙着操辦起了婚事。就在這節骨眼上,又在路上碰到了我的同學。
我心裡還惦記着我們的“高科技產品”,也不知道“老大”買了衝鋒槍沒有,於是問他,“那事到底最後怎麼樣了?”
他一臉苦笑,“黃了,真倒霉, Pachinko 更新換代,把數彈子機都換成新的型號了,我們的發射器一次也沒用上。”
聽了這話,我反而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,不管他講的是真是假,反正我是不想再趟這個渾水了。他也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的意思,話鋒一轉,問道,“最近在忙些什麼?”
“啊,忙着準備結婚吶。” 我答道。
“行頭置辦得怎麼樣了?西裝領帶皮鞋,都有了?”
“都是原來從國內帶來的,日本的衣服太貴了。”
他眼睛一亮,“結婚是人生大事,不能太隨便了。這事你別管了, 包在我身上。”然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,“我們倆身材差不多,你跟我來。”
跟着他來到東京最繁華的銀座,到了一家服裝店門口,他把手中的塑料袋往我這兒一塞,說,“你在門口等我一下,我去去就來。”說完,整了整衣服,挺起胸,氣宇軒昂地走了進去。我心裡隱約猜到又有事要發生了。
果然,二十分鐘之後,他腋下夾着個公文包,鼻子上多了一副眼鏡,西裝革履,一身名牌地走了出來。他不緊不慢地來到我跟前,說,“別發獃了,走吧。”
我站在那兒,目瞪口呆。
晚上,我迫不及待地給未婚妻打電話,“Honey,我結婚的行頭置辦齊了,都是日本的名牌。”她嗔怪道,“花那麼多錢幹什麼?我們在上海的婚禮還要一大筆錢呢。”我喜滋滋地說,“別擔心,猜猜我是從哪裡搞來的。”“猜不出。”“實話告訴你吧,這是我同學從銀座的名牌店裡偷出來的。”“What?”這回輪到她目瞪口呆了。電話那頭沉默良久。“怎麼啦?”我問。她遲疑了一下,終於開口了,“你以前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。”
放下電話,我陷入了沉思,我這是怎麼了?幾年前我還自認是個有志青年,為了國家和民族,一腔熱血,上街遊行,要清除腐敗,要打倒官倒,夢想建立一個民主公正富強的社會;幾年過後,我竟然淪落到了黑社會的邊緣 …… 我的心裡一片迷茫,只有一個念頭,“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,我要有一個新的開始。”這好像是我唯一可以抓住的那一根稻草。
現在回頭看,在日本的這段經歷,對我後來願意接受基督教有着很大的影響。許多中國人接觸基督教,常常無法接受的一點就是,基督教認為人人都是罪人,人裡面有罪性。這和儒家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是不同的。而對我來講,這一點卻完全不成為攔阻,因為我知道,我之所以從小到大還算個好孩子,就是因為上帝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環境,有好的父母,好的老師,好的同學,要想變壞也難。可是換了一個環境,稍稍多一點誘惑,我裡面的罪性就如此地滋生壯大,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可也就是這麼一點點的自我反省,讓我在那一位公義的神面前不由自主地謙卑下來,不再那麼理直氣壯。就像美國人常常講的,“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,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.”
當然,前提是真的有這樣的一位上帝存在,要讓一個從小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,滿腦子邏輯,證據,進化論的我去相信的確有神,絕非易事。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,晴空萬里,一架波音737客機緩緩降落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Albuquerque機場。我和妻子終於在美國團聚了。
一個月之前,我第三次踏進了日本的美國領事館,遞上我被拒簽了兩次的護照。 給我簽證的女簽證官翻了翻我的簽證紀錄,緩緩地對我說,“對不起,我不能給你簽證。”我心裡一沉,她接著說,“因為我上次對你拒簽了,為了公正起見,這一次,我請我的同事來審閱你的材料。”嚇死我了,不帶這麼大喘氣的。
轉到另一個窗口,是一個高高瘦瘦的金髮俊男,他看了看材料問,“你去美國幹什麼?”我答,“我妻子在美國念書,我想拿F2簽證去陪讀。”“按照規定,我不能給你F2簽證,因為你有移民傾向。”他頓了頓,向我眨了眨眼睛,“不過,你在日本的工作很好,公司背景也強,你可以申請旅遊簽證去美國,你願不願意?”我幾乎要感激涕零了,因為他的一念之慈,我的人生軌跡從此被改變了!
臨走前一晚,我們一同赴日的幾個好朋友相聚在上野的一家中國餐館,為小z舉行告別晚宴,因為第二天一早,他就要離日赴美了。我當時掙扎了許久,要不要向一班好友透露,我也要走了,我的航班和小z只相差2、3個小時。但是我還是忍住了,我不想在最後一刻,節外生枝。
我的謹慎其實並非多餘,後來才知道,我和小z的同時離去在當時震動極大,公司當局一直追查我們的下落,直到最後動用了關係,查明小z飛赴紐約,我在休士頓入境美國,才算罷休。隨後,公司又企圖收繳所有公派同學的護照,引起大規模的抵制,這些都是後話了。
現在想來,真是強扭的瓜不甜,若中方領導當年不強行送我去日本,也就不會有兩年後這場“逃出日本”的鬧劇了。其實公司待我們還算不錯的,真的把我們當成人才來用,給他們帶去那麼多的麻煩,實在是有點對不住他們。
離開日本,我的感覺就好像鳥兒飛出了籠子一般,在Houston過關的時候,海關的官員問我來美國幹什麼,我說,“我妻子在美國念書,我來看她。”他說,“你的簽證搞錯了,B2簽證只能在美國待一個月,我無法給你更多了,你趕緊找律師換成F2簽證吧。”剛剛踏上美國國土,我就深深地被普通美國人的善良仁厚,通情達理感動了。
在Albuquerque最先認識的美國人是道生教授和他的妻子琳達。道生是美國Sandia國家實驗室的資深科學家,也是新墨西哥大學的客座教授,矮矮的個頭,兩道濃眉,臉上永遠帶着和藹可親的微笑。他是我太太的老師,拿她當作自己的女兒一般,也就是他們兩口子把我們帶進了教會。
說實在,我走進教會的動機實在是非常功利的,一方面是感激道生夫婦對太太的照顧,盛情難卻,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教會裡多和美國人打打交道,練練口語。所以牧師講的我基本上是一個耳朵進,另一個耳朵出,什麼都沒記住。而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道生教授這個人。
原來以為信教的人,都是些沒有文化的老太太,要不就是失戀的,失意的,失望的加上失敗的。從來沒有想過象道生這樣的傑出科學家會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,後來慢慢地才知道結婚之前道生是不信神的,而琳達卻是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,結婚之後,為著信仰的不同,兩人屢屢發生衝突。從小循規蹈矩的琳達哪裡是能言善辯的道生的對手,常常被道生嗆得啞口無言,最後有一天,琳達對道生講,“好了,我們不要再吵了,你是一個作研究的人,最講究用證據說話,你去找證據來證明我信錯了,我就聽你的。”
於是道生就真的花了幾年的時間去研究,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道生最後決定信主了。因為他看到的證據讓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信仰歸宿。
雖然道生提到的那些證據對我來講,實在是聽得個一知半解,稀里糊塗,但是他的學識和為人卻讓我從此對基督徒刮目相看。
在Albuquerque的那幾個月,快樂而又忙碌。買舊車,學駕駛,考執照,找工作,申請學校。生活充滿了等待和期盼,終於在夏天開始的時候,一家遠在麻州的保險公司給我打來了電話,聊了幾句之後,發現我在日本做的軟件開發和他們這裡的完全一樣,於是連面試都省了,直接就決定錄用我。而且他們願意替我辦綠卡,這樣身份問題也解決了。那幾天就好像在做夢一般,我和太太都無法相信我們會如此地幸運,因為那時其實internet還沒有起步,美國經濟也不景氣,許多留學生畢了業,卻因為身份的關係找不到工作,只好繼續讀博士或者做博士後。91年底愛荷華大學的盧剛事件,起因就是盧剛畢業後找不到工作,結果遷怒於他的教授和同學,槍殺6人之後,飲彈自盡,這是題外話了。
我找到了工作,太太也碩士畢了業,我們就要告別朋友和導師,離開永遠陽光明媚的Albuquerque了。得知我們要走了,道生夫婦依依不捨,拉住我太太的手,問她願不願意在走之前受洗,成為基督徒。她不假思索地回答,“我願意。”我倒是吃了一驚,這種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。
回到家,我問她,“你真的要受洗啊?”
她說,“是啊,他們說信耶穌可以上天堂,要是有天堂,我是要去的。”
“那我怎麼辦,你就這樣扔下我,一個人去天堂?”我半開玩笑地問。
“你要想去,你也可以受洗呀?”
我啞口無言。對一個根本不相信上帝,不相信天堂地獄的人,受洗對我沒有任何的吸引力,但妻子願意,我也無所謂,只要她高興就好。讓我吃驚的倒是教會裡的人歡天喜地的樣子,好像過節一般,妻子受完洗,大家紛紛送上禮物,興高采烈。當然最高興的是道生夫婦,送來了一大簇的鮮花,拉着我太太的手,說著祝福的話,臉上流露出發自心底的喜悅,渾身散發著愛的光輝,那一刻,讓不信神的我也被他們的真摯所感染,被愛的感覺真好。
要離開了,心裡依依不捨,但又充滿期待,因為我們的美國夢即將要開始了。此外,心裏面還有另外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,沒有了道生夫婦,我就再也不必為去不去教堂糾結了,再說太太也受洗了,她天堂的門票也拿到手了,我的教堂生涯也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了吧。
94年夏天,把一家一當--四隻大旅行箱塞進那輛白色的Hatchback,我們就上路了。一個星期的時間,我們走走停停,橫穿半個美國,來到了東岸。感受最深的就是放眼望去,到處是鬱郁蒼蒼的樹木,滿目蔥蘢,和新墨西哥一望無際的灰黃形成巨大的反差。這裡有山有水,有花有草,在往後的二十年里,美麗的新英格蘭成為了我們的第二故鄉。
拿到了第一個月的薪水,忽然發覺我們好有錢,於是兩個人決定吃遍Boston的中餐館,一個星期一家,好不自在。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快樂地過着,我們早已把教會的事忘到九霄雲外了,直到有一天,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:“請問,這是不是徐先生,徐太太的家。”
“是,請問您是哪一位?”
“啊,我是這裡華人福音堂的章開第傳道,你們的朋友道生夫婦委託我向你們問好。也歡迎你們到我們這裡的華人教會來看看。”
道生夫婦還真有心,千里之遙居然還輾轉找到這裡的華人教會,委託他們來照顧我們。在章傳道的力邀之下,我們再一次踏進了教會。
畢竟中文是母語,到了華人教會就好像有回到了家的感覺。第一次正好是教會的徐長老在講解創世紀伊甸園的故事,我從來是把亞當夏娃的故事當作神話來看待的,可是這位長老居然能把這一段講得頭頭是道,像是真的一樣,這對我來講可謂是一次啟蒙,原來基督徒是這麼解讀聖經的,他們是把聖經的記載都當作真實的歷史來看待,而且他們宣稱聖經是神向人的啟示,所以“聖經無誤”。這激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心和好勝心,我心想,我就不信這裡面會沒有絲毫的紕漏,我的讀經生涯就這樣開始了。

秋天的時候,太太在耶魯附近找到了工作,和我的公司相距150英里,思來想去,最後決定替她在耶魯附近找處小公寓,這樣至少我們周末可以在一起。這事讓教會裡的一位在康州工作的弟兄知道了,就自告奮勇地要帶我們去那邊找房子。
那年代沒有互聯網,你要找房子必須到那個地方,找到當地報紙的星期日廣告版,然後一個一個打電話過去問,要是當地沒有熟人的話,是非常不方便的。
我們找了一個周六,搭這位弟兄的車來到了康州他的一位姓孫的朋友家中,當晚就在孫弟兄的家中住下了。孫弟兄兩口子是從台灣來的基督徒,兒子剛上大學,我們就睡在他們兒子的房間里,孫太太是個能幹的家庭主婦,熱情好客,給我們看她兒子的各種照片和獎盃,和我們聊家常,待我們彷彿是遠道來的親戚一般;孫弟兄黝黑的皮膚,瘦瘦高高的一個人,要講的話一大半都被太太搶去了,於是只好看着我們笑,非常可愛的一家人。雖然我們相差了十多歲,又是海峽兩岸不同的背景,可是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他們,這是真誠和善,讓你可以信任的一家人。
第二天一早我們醒來,孫太太已經做好了早點,久違的豆漿和包子,在飯桌上冒着熱氣,旁邊放着當天的報紙,厚厚的一疊廣告,正是我們需要的。
我心裡暖暖的,在日本也好,在國內也好,經歷各種的爾虞我詐,勾心鬥角,奉行的是見人只說三分話,未可全拋一片心,總是提防着不要被人騙了,或是被人佔了便宜。而在這裡,我看見卻是教會裡的人,對你完全地接納,不問你的身份地位,只要你有需要,他們就願意盡他們的力來幫你一把。我相信這正是基督教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在孫弟兄夫婦的幫助下,我們很快在New Haven附近找到了房子。一間小小的公寓,一張飯桌一張床,再加上兩把椅子,就是全部的傢具了,雖是簡陋,但卻是一個溫馨的家。每個星期五下了班之後,我就從麻州開兩個半小時,回到New Haven的家,然後星期一的早晨,起個大早,再往回趕。雖然辛苦,但因為年輕,所以也不覺得什麼。只是遇上風雪天就比較麻煩,有一次遇上暴雨,把雨刷開到最大檔,還是看不清前面的路,只能依稀跟着前車的尾燈往前蹭,最後索性把車停在了高速公路邊,看着車窗外的狂風暴雨,一籌莫展。
更討厭的是大雪天。那次是星期一大清早,我心急慌忙往公司趕,結果車子打滑,擦到了停在路邊的一輛車。天還是烏黑烏黑的,路上一輛車也沒有,藉著昏暗的路燈,我查看了一下受損情況,我的車倒還好,只是車前方右側的擋板有些擦痕,而對方的車就慘了,左前門被撞變了形。我站在那裡猶豫了幾秒鐘,一個聲音在說,“要不要留下電話地址,告訴人家是你撞的?”另一個聲音卻道,“本來就是輛舊車,留下電話,會不會被人家獅子大開口訛詐?反正沒人看見,快溜吧。”終於良知的聲音被壓下去了,我鑽進車子,倉皇逃離了現場。
到了公司,同事看見了我的車受損,關心地問我,“出車禍了?”,我只好支支吾吾地說,“嗯,不小心自己撞到了牆。” 一個謊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謊言來遮蓋。
這之後,每當我看見聖經上講,“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”,講到魔鬼“本來是說謊的,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”我就心裡一顫,總覺得冥冥之中有一雙眼睛在注視着我,無聲地見證着我的虧欠。
多年之後,上帝給了我第二次的機會。太太倒車撞到了停在路邊的車,這一次,我老老實實地敲開了人家的房門,“對不起,我們不小心撞到你的車了。”沒想到車主人查看了一下傷痕,竟然大度地對我們說,“沒關係,一點點擦傷,我自己處理就是了,要是花費太大,我再找你們,好不好?”
除了謝謝,我真不知道再說什麼好了。對我來講,這不堪的一頁終於翻過去了,上帝讓我看到,即便是做老實人,也不一定就會吃虧。
在紐黑文的那段日子裡,生活簡單,但不枯燥。周五的晚上就去孫弟兄的家,有聚餐,有查經。孫弟兄話不很多,人卻極其真誠,慢慢知道了他原來是修行很深的佛教徒,花了很多的時間鑽研佛經,最後卻變成了基督徒。於是就很有興趣想知道他為什麼會改變信仰的。
他說,“信佛讓我向善,可是我卻發現自己沒有行善的能力;基督教不僅讓我向善,而且給了我行善的能力。”
他講的前半句我大至可以了解,這讓我想起當年白居易和鳥窠禪師的一段對話:
白居易請教大師佛學的精義,鳥窠禪師給了他八個字:“諸惡莫作,眾善奉行。” 白居易聽後哈哈大笑,“這個道理,三歲小兒都知道。”大師回答:“三歲小兒雖道得,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
講的也許就是這種無力行善的困境吧。可是孫弟兄的後半句話,我完全無法了解。於是他就給我解釋,這是一種從神而來的能力,做人所不能的事情。
他講有一次他去探望一位台灣老將軍,兩個人聊到基督信仰,孫弟兄就講人都是罪人,這下把將軍惹毛了。他挺直着腰板,大聲說,“我二十歲投筆從戎,為國為民,捨身忘死,上對得起天,下對得起地,我不是罪人!”孫弟兄當場就楞在那裡,不知道說什麼好了,然而心底里卻不知為什麼湧起一種悲憫的情緒,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流,他本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,可是那一次不知怎麼了,對自己拚命說不要哭,可眼淚就是停不下來,就這樣不知過了多久,結果老將軍長嘆一聲,說,“你是對的,我是一個罪人。” 原來將軍年輕時曾辜負過一位女子,這事一直在他心底存着,從來沒有向人提過,而那一天,將軍向孫弟兄和盤托出,最後竟然在孫弟兄帶領下信主了。事後,他誇孫弟兄,“你真會講話,竟然把我說動了。”
孫弟兄笑着對我說,“其實那一天我基本就沒講什麼話,只是神的靈在那裡做工,感動我,也感動老將軍,讓他信了主,這就是我講的從神那裡來的能力。”
孫弟兄的故事,對我是一個衝擊,難道真的是有超自然的能力,真的有神?
我是學理工科的,多年的訓練讓我對任何事都不會輕易相信。對任何的宣稱,我們不但要看證據,更要看證據的可靠性和相關性。
舉一個例子,我在教會認識的一位朋友,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看見她,最近在一次燒烤的聚會上碰到了,彼此問候之後,我就問她,“怎麼好久都沒看見你,還好嗎?”
她說,“現在還好,前兩年生了一場大病。”
我問,“怎麼了?”
“腦子裡生了個瘤,美國醫生都沒什麼辦法,後來是朋友介紹,練了**功,瘤子就沒有了。所以我現在信**功了,也替他們做一些義工,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
於是我們就聊了起來,其實我很理解她的選擇,這種神跡般的醫治,對人的世界觀的衝擊是無與倫比的。可是,站在朋友的立場,我不得不告訴她,她的選擇可能會有問題。因為她認定是跟着師傅練功,才醫治了她的疾病,這裡的因果關係其實並不那麼確定。我有一些朋友是從事癌症藥物開發的,從他們專業的角度來講,判定一個藥物是否有效,看一個個案是完全沒有意義的,人體有許多的機能我們還不明白,有些人會對不含任何有效成分的安慰劑有反應,也許是某種心裡的作用,有時也能得醫治。所以判定一個藥物是否有效,最好是用雙盲試驗,醫生和病人都不知道用的是安慰劑還是真的藥物,這樣出來的結果才會有意義,才能判斷這個藥物是否真的有效。
當然對我這位朋友來講,她不見得關心練功的醫療效果,即便在其他人身上沒有任何效果,可是對她來講,她得了醫治就夠了,用她的話來講,也許就是因為她是有緣之人。
這就牽涉到許多人都有的第二個誤區,就是認為靈驗的一定是從神那裡來的,從她的觀點來看,因為練了大法,病得醫治,所以*大師講的就一定是對的,是宇宙的真理,真神的化身。其實,各大宗教都有神跡奇事,佛教,基督教,伊斯蘭教,甚至連一些明顯的邪教都有神跡發生。站在基督教的立場,這不足為奇,基督教認為神跡,或者超自然的事會發生,除去騙人的把戲和人為的巧合,無非有兩種可能:一種是從神那裡來的,一種是從魔鬼那裡來的。這兩種靈界的力量都能做人所不能的事情,只是人常常輕信,以為神跡就一定是從神而來,其實不見得。聖經講的好:“一切的靈,你們不可都信,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。”
回到孫弟兄講的故事,雖然讓我感動,但是讓我象老將軍那樣就這樣信主,我覺得還有不夠的地方,我需要實在的證據。如果說道生夫婦,讓我對基督徒心生好感的話,那孫弟兄就是我信仰的引路人,因為從他的書架上,神讓我找到了我要看的證據--麥道衛(Josh McDowell)寫的《鐵證待判》。

《鐵證待判》的作者是學法律的,他好像道生教授那樣,接受人家對他的挑戰,去考察耶穌說自己是上帝兒子的宣稱,結果他找到許多前所未知的歷史證據,寫成此書。他從法律審判的角度來檢視這些人證物證,從而得出結論,你無法只把耶穌當作一個偉大的教師或聖人來看待,因為他的宣稱太過驚世駭俗,耶穌若不是瘋子,騙子,那你就不得不相信他的宣稱,他是神的兒子。
看完此書,讓我對基督教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,那不是一個只訴求於你的主觀經歷的信仰,不是講緣分,也不是講慧根,它有實實在在的證據擺在那裡,任何人只要你願意,都能夠認識這一位神,就好像耶穌講的,“你們祈求,就給你們;尋找,就尋見;叩門,就給你們開門。”
在孫弟兄的幫助下,我對基督教的認識逐漸加深。而另一方面,一個冬天的奔波,讓我們決定還是搬家住在兩人公司的中間地帶,這樣雖然辛苦一點,但至少可以每天在一起。開春的時候,我們離開紐黑文,搬到了康州的首府Hartford。我每天單程開車90英里(145公里),太太單程60英里(97公里),仗着年輕力壯,就這樣開始了我們“瘋狂的旅程”。
那時在孫弟兄的介紹下,我們找到了Hartford的一家華人教會,從那裡借了許多佈道會的磁帶在開車的時候聽。在我每天單調的旅程中,這些磁帶帶給了我許多的歡笑,鼓舞和思考,每天晚上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和太太分享白天聽到的信息,互相探討切磋。到了星期五的晚上,我們拖着勞累了一周的身體來到那間華人教會,聽帶查經的弟兄講解聖經,和大家辯論,等到結束,走出教會的時候,身心的疲乏竟然完全被洗去,人好像重新充了電一般,就這樣星期五晚上的聚會成了我每周的期盼。現在回頭想來,神實在是恩待我,讓我有渴慕的心去尋求他,也藉著各種各樣的人來回答我心裡各種各樣的問題。而其中一直困擾着我的,就是關於靈界的問題。
小時候最害怕又最愛聽的,莫過於奇奇怪怪的鬼故事了。夏天的晚上,吃過晚飯,搬只小凳子,坐在弄堂深處,聽隔壁鄰居家的大孩子,講《一隻繡花鞋》,《綠色的屍體》之類的嚇人故事,在那悶熱的夜晚,給人後背帶來一絲絲的涼意。
在中國的民間傳統里,認為人死後就變成鬼。好人變好鬼,如果受大家愛戴的,可能還會升格成神仙,象關羽,包拯一樣;而壞人死後變成惡鬼,有時還會為害人間,需要有道士和尚來制服他們,所謂“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”就是這個意思。到了天朝初期,破除一切封建迷信,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深受無神論教育的影響,對一切鬼神之談往往嗤之以鼻 。所以許多人看到聖經中描述耶穌趕鬼的故事,就象看聊齋志異一般,只是把它當成民間傳說故事來看待。
我當然也不例外,在查經班屢屢挑戰老師的底線,成為教會有名的問題兒童。直到有一次,我們在熱烈討論靈界的真實性的時候,往常和我站在同一條戰壕里的慕道友小C,突然反戈一擊,說道,“我相信靈界的存在。” 於是小C就給我們講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:
小C是練氣功的,雖然來教會之後,有人提醒他練氣功有一定的危險性,他根本就沒放在心上。有天晚上,他和往常一樣打坐練功,漸入佳境之時,忽然看見一隻右手從空中浮現,朝他的心口逼近,並且作勢要掏他的心,這一下把小C嚇得魂飛魄散,情急之下,他想起教會的人曾經對他講過,在危難的時候,可以向耶穌禱告。於是他脫口而出,“耶穌救我!” 說時遲那時快,從天上彷彿降下一隻巨手,一下子就把那隻鬼手給提走了。
小C的故事,讓我開始對靈界的真實有所了解。後來陸陸續續又聽了梁燕城,張佳音等人的靈界經歷,看了小光寫的《衝破靈界的黑暗》,讓我慢慢接受了聖經的觀點。
聖經對靈界的事着墨不多,但看法和中國民間傳統大不相同。基督教認為人死後是不會變成鬼的,而是處在一種等待的狀態,直到神最後審判的那一天。在上帝所創造的所有活物中,最完美的是天使長,而這一位天使長卻選擇背叛,率領三分之一的天使反對神。這一位天使長就是後來人們耳熟能詳的撒旦魔鬼,和它一起背叛的天使就是眾邪靈。這些靈界的邪靈具有超自然的能力,他們有時禍害人,有時也選擇“做好事”,但是目的都是一個,就是要讓人遠離上帝。它們最後的下場,是在審判之日被扔進火湖,面臨永遠的死亡。
寫了這麼多靈界的事情,希望不要給大家帶去不安,請記得小C的故事,神比他所造的一切活物都大,在危難的時候,記得向耶穌禱告。
有些人會問,“你有沒有經歷過神跡?” 聽過許多其他人的見證,可是發生在我身邊的,我有十分把握的,也許只有一次。
那是我們剛信主不久,有一次太太要回國,結果在走的前一天感冒了,喉嚨疼得火燒火燎,晚上她睡不着,於是就起來,跪在窗口向耶穌禱告,“主啊,我明天就要坐飛機回去,還想把福音傳給我的家人朋友,可是現在這個樣子,我真的擔心連上飛機的力氣都沒有了。主啊,求你醫治我。”
基督徒也許都有過類似的禱告,我們也知道“這病不至於死”,遲早都會好的,許多的時候我們禱告,只是想要一點從神那裡來的平安,可以讓我們好受一些。可是,那一個晚上,神跡發生了。
當她禱告完,人還跪在那裡,沒有完全站起來的時候,忽然好像有一個冰塊從她的喉嚨里通過,冰涼冰涼的,她人一下子站了起來,把我推醒,帶着一種驚奇興奮而又有些害怕地對我說,“神醫治我了,神真的就在這裡。”
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神在那一個晚上用神跡醫治她,也許是因為我們剛信主不久,神要藉著這來讓我們知道他真實的存在?因為那時候,我曾經有過這樣的疑問,世上這麼多的人禱告,神哪裡管得過來?況且這個要出太陽,那個要下大雨,神聽誰的好?一個老弟兄就對我講,“神就是有這個能力,他聽得到每個人的禱告。但是神不是我們得僕人,他憑着自己的旨意行事。”
後來慢慢地我才明白禱告更多的是和神建立一種親密的關係,就像談戀愛似的,兩個人關係好的時候,無話不談,只要在一起就是一種幸福和滿足;如果只是需要幫忙了,才去找你的對象,那這兩人的關係多半有問題。和神的關係也是如此,若只是有了需要才去求神,那你信的,其實是阿拉丁神燈的神,是你的僕人,不是你的主宰。
就這樣,我對神的認識越來越多。有一天,太太問我,“你現在有幾分相信?”
我說,“大概百分之八十吧。”
“那你要不要考慮受洗?”
我搖搖頭,“你是知道我的,最煩教條的東西了。況且聖經上講,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拜神。我只要心裡相信就可以了,不用走這個形式了吧。”
受洗的事就這樣耽擱下來了。每天還是照常聽着佈道會的磁帶去上班。這一天聽的是徐華醫生的講道。在90年代的時候,徐華大概是在海外留學生中傳福音最受歡迎的一位講員,他本來是做麻醉科醫生的,在事業頂峰的時候出來傳道,帶領無數的人信主,當年頗有今天唐崇榮牧師的影響力,而且兩個人的風格也挺像的,幽默強勢,咄咄逼人,和人們印象中牧師溫文爾雅的形象大相徑庭。可以看得出,他信主以前一定是個眼高於頂,非常驕傲的人。有一次講道,他對着下面一班的留學生說,“不要以為你聰明,永遠拿第一,那是因為你和我沒有在一個班,有我在,你絕對別想拿第一……” 我們當年這批自視極高,氣焰囂張的留學生,也許正是被他的氣勢所壓倒,又為他的口才和學識所折服,最終一個個在他的帶領下信了主。
這一天,不知為什麼,徐華忽然把炮火對準了那些自稱信耶穌,卻不肯受洗的人,“你算老幾,竟敢說你不用受洗,連耶穌基督都受了洗,你自稱為耶穌的信徒,倒不用受洗了?” 這話正中我的要害,對呀,既然我認為自己是信耶穌的,憑什麼我就可以不聽耶穌的吩咐,自說自話不用受洗了呢?那一天的感覺,就好像神藉著徐華醫生的口,把那一篇道講給我一個人聽。我無法再找借口了。
到了星期五,來到教會,我乖乖地找到了牧師,說:“我願意接受洗禮。” 牧師反倒嚇了一跳,沒想到我這個不安定分子,居然自己提出要受洗了。可是下個主日就是浸禮,照理受洗的基督徒是要先上幾個星期的受洗班的,總算牧師法外施恩,願意破例為我補課。好在我大部分的問題都在這幾個月的上班途中解決了,於是順利過關。
1995年5月14日,母親節。我和另外三位慕道友一同受洗,歸入主名。從浸池裡出來,天好像沒有更加地藍,草也沒有格外地綠,我還是原來的我,但神的聖靈卻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到我裡面,我生命的改變即將開始了。
洗禮完畢,牧師照例要祝福,輪到我時,他忽然打破常規,說起預言來,“弟兄,神讓你這麼辛苦,每天長途開車並不是偶然的,神要用這段時間,讓你可以聽他的話語,帶領你歸向他。如今你已經信主受洗,神的工作要告一段落了,我想你和你太太,過不了多久就不用這樣長途跋涉了。”
一個月之後,太太工作換到了麻省,我們終於不用再長途跋涉了,牧師的“預言”應驗了!
這是我們在十二個月里的第五次搬家了,從新墨西哥州開始,我們每搬一次家,就好像要離神遠一點,可是他的慈繩愛索卻緊緊地把我拉住,讓我一步一步走進他的懷抱。回頭去看,神好像是一個最有耐心的父親,儘管我一次次地質疑,頂撞,甚至褻瀆他,他卻用他的愛吸引我,差遣他的僕人一個一個地為他作見證,道生夫婦,開第傳道,講解亞當夏娃的徐長老,開車送我們去康州的若珍弟兄,孫弟兄夫婦,梁燕城,張佳音,徐華醫生。。。難怪聖經羅馬書中這樣描繪神的愛:
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,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。為義人死,是少有的;為仁人死,或者有敢做的。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,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
而這才是個開頭,在以後的十八年里,神的恩典在我們的身上,可謂數算不盡。超自然的神跡也許我們只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一件小事,可是若仔細去想,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改變,這本身豈不就是最大的神跡嗎?俗話說得好,“江山易改,本性難易”,要能真正改變一個人,也許真的只有神的大能才可以做到。
我的性格是很急躁的,最明顯的就是反映在開車上面。上了高速,我好像穿上了盔甲的騎士,風馳電掣,所向披靡。在信主的頭幾年裡,我平均是一年兩次車禍,一張罰單。可是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有錯,被我超過的車都開得太慢,根本就不應該在快車道上;把我超過的車都開得太快,統統應該被警察開罰單。神藉著兩件小事讓我改變:
有一天,我在Masspike上飛車疾馳,到了收費站,一長串的隊伍,我正心浮氣躁,心裡痛罵著州政府收刮民脂民膏,一個Big Dig挖了十五年,大大超出預算,只好用高速收費補虧空。這時一輛小車乘我一不留神,嗖地一下插到了我前面,我是氣不打一處來,重重地按下了喇叭,嘟了他足足半分鐘。可是插都插進來了,你有什麼辦法,只好眼睜睜看着它在我前面過了收費站,揚長而去。輪到我了,我把車開了上去,收費員向我揮了揮手,示意我走,我心裡納悶,州政府良心發現,不收費了?“Hi, what’s going on?”我問。“Oh, the guy in front of you has already paid the toll for you.” 原來前面那輛車可能有什麼急事,插了我的隊,感到不好意思,就替我把錢交了。我真是百感交集,忽然意識到我這個基督徒做得實在不怎麼樣,好像神在給我講,“不要總是論斷人家,要多一點謙讓寬容的心。”
幾天之後,我舊病複發,在高速上和一位老兄飆車,你不讓我,我不讓你,把坐在身邊的太太差點氣哭了,我也是一肚子氣,每次我和人在路上有爭搶,她總是站在我的反方,這日子簡直沒法過了。回到家,誰也不理誰,我進了書房,關上門,坐了一會兒,不知為什麼,心裡有一個衝動讓我跪了下來,我剛一開口禱告,眼淚嘩地一下流了出來,心裡對自己的衝動魯莽萬分懊悔。要知道我已經是N年沒有哭過了,上次去眼科醫生那兒檢查,醫生說我淚腺有些堵塞,而這下應該是完全疏通了。正哭着,太太走了進來,手裡拿着一個削好的水果,原來她在另一個房間禱告,神的靈也感動她,讓她來和我道歉,不該總是給我火上澆油。這事之後,我在高速公路上的表現是可圈可點,連續多年無車禍無罰單,神就這樣改變了我。
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,神對我的改變是全方位的,在夫妻關係,金錢奉獻,教會事奉,各方各面,聖經好像是神寫給人的一本使用手冊,教導我們為人處事之道,讓人一生行在神的光中。可以寫的也許還有很多,只是到這裡應該可以告一個段落了。若是你要問,為什麼我的運氣這麼好,神這麼恩待我?我要告訴您,這個福分您也一樣可以得到。聖經上說,
你們祈求,就給你們;尋找,就尋見;叩門,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,就得著;尋找的,就尋見;叩門的,就給他開門。
而且神所給的,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,因為“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,耳朵未曾聽見,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”(哥林多前書2:9)
願神祝福您!
cgcm_media July 17th, 2023
Posted In: DevotionTestimony, Testimony